2017年12月28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颁奖典礼上,北大校友、旅匈作家、翻译家余泽民翻译的《烛烬》荣获“翻译长篇小说奖”,原创获奖作品为刘庆邦的《黑白男女》、吕新的《下弦月》、陈彦的《装台》和曹文轩的《蜻蜓眼》。
 余泽民
余泽民
吴承恩为明代文学大师,《西游记》作者,江苏淮安人。据悉,“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由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委区政府、《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江苏省作协共同举办,旨在弘扬吴承恩的卓越文学成就,促进长篇小说创作的持久繁荣。获奖作品从2015至2016年间出版的230部作品中选出,体现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与翻译的丰硕成果。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坤、李东华,文学评论家何平,著名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以及淮安市政协、文联负责人和获奖作家、获奖代表等50余人参加了颁奖典礼。
余泽民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1991年赴匈工作,现定居布达佩斯,多年来致力于匈牙利文学翻译与个人创作,翻译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马洛伊等作家作品近20部,创作小说、散文10部,先后获得“21世纪文学之星”“中山文学奖”及台湾“开卷好书奖(翻译类)”和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近年,余泽民还从文学翻译专业的教育工作,担任北京北二外中欧语学院特聘讲课教授,同时在匈牙利的罗兰大学、鲍罗希学院担任文学翻译专业课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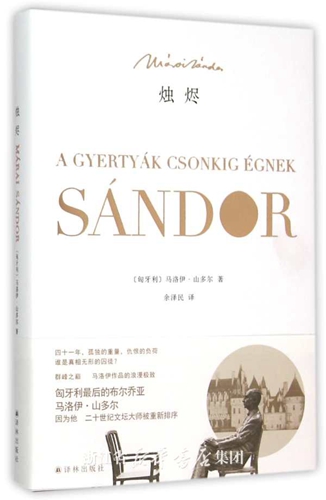
《烛烬》书影
这次获得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翻译奖的作品《烛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匈牙利作家马洛伊的代表作。马洛伊是20世纪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诗人,科学院院士,被誉为匈牙利“民族精神的哺育者”和“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继承人”。他在长达7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论和日记60余部,精细描绘了20世纪欧洲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画卷,忠实纪录了东欧知识分子苦难复杂的心路,深刻反映出一个世纪的平民化过程与传统价值沦丧的关系,为逝去的帝国荣光和贵族精神唱挽歌。1948年他流亡西方,1989年2月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生命。冷战期间,他的作品在匈牙利被禁,去世后才解禁,并被匈牙利政府追授“科舒特奖章”,并设立“马洛伊文学奖”,他被视为近些年世界文坛的重要发现。《烛烬》最能表现他高贵、孤傲的精神世界和庄重、华美的文学风格,以莎士比亚式的纯粹到诗性的艺术语言,通过两位老人41年后重逢和回忆讲述了一个多层次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歌颂了至高无上、但已难幸存的人类友情。
定居布达佩斯的余泽民先生未能回国亲自领奖,特委托译林出版社编辑赴京代为领取奖牌和奖状,并以书面的形式发表了答谢辞。(文/傅冬红)
答谢辞:文学与文学的对话 (余泽民)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好:
当我意外地通过微信获知《烛烬》被授予翻译奖的消息时,我刚好和家人一起从布达佩斯来到奥地利蒂罗尔州的一个小山乡里过圣诞节,这里空气明远,祥云飘卷,远处是瑞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峰,敲击键盘的碎响都跟在都市里不一样。我将这个消息视为天使专为我报来的福音,在欧陆最温馨的时节里,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好的礼物。
遗憾的是,我来不及赶回国亲自领奖,好在译林出版社我的两位编辑好友姚燚、张睿乐意从南京赶来代我出席,想来这荣誉也有他们一份,他们的慧眼识珠、耐心编辑和用心推介也都是中文版《烛烬》的一部分,我请他们代我发言,由衷感谢吴承恩文学奖评委会老师们的工作和对这本译著的认可。我甚感荣幸,且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不仅因为《烛烬》确是一部好长篇,是我翻译生涯中最倾心最满意的一部,而且,我还愿把这个翻译奖视为:文学与文学的对话,经典向经典的致意。
吴承恩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虽然出生在灌输理想、禁锢想象、文学贫瘠的60年代,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一本“集体创作”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让我看得着迷,而后,我又囫囵吞枣地读了“破四旧”后家中幸存的一套线装版《西游记》,至今我都对薄脆、泛黄纸页里的版画插图记忆犹新。无数次,晴天或阴天,我坐在北京西城一座大四合院大北房高台阶的宽门廊下,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捧着《西游记》看变幻的浮云,幻想哪一片后是金盔金甲的天兵天将,猜测那一朵是眨眼间能飞出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偷偷开拓出一个虽然简单幼稚,但也自由丰富的想象空间。
不光于我,吴承恩于匈牙利人也不陌生。早在1969年,匈牙利第一位汉学家陈国先生(Csongor Barnabás)就把它翻译成了匈语,书名译为《西游记,猴王的故事》(Nyugati utazás, avagy a majomkirály t?rténete I–II.),半个多世纪来一版再版,影响了好几代匈牙利读者,最新版本是今年春天上架的,封面是红色剪纸的孙悟空。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著名版画家库瓦奇·托马什(Kovács Tamás)生前凭借奇特的想象,创作了一套极其工细、形象生动的铜版画插图。几年前,匈牙利总理访华,匈方特意请我参与编辑工作,并将这些插图制作了一套中匈双语版《西游记》作为国礼送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既是文化外交的一段佳话,也是对文学翻译意义的又一见证。
人类交流,离不开翻译;了解世界,离不开文学。我上小学时,虽然社会并不倡导读书,但我还是幸运地读了不少。当时,我在北京三十五中上学的表姐兼做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可以把库里蒙尘的旧书搬回家读,而且都是竖版、繁体字,比如苏联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将计就计》和《夏伯阳的故事》,还有后来才知道是名著的《地心游记》《俊友》《红与黑》和《高老头》。尽管那些书读得一知半解,但也拓展了视野和想象力。
在表姐影响下,我还从读书迷到抄书。她花一年时间抄完了《牛虻》,我一笔一划地抄下了《安徒生童话》,从那之后,印在“工作日记”牛皮纸皮上的红字语录和蓝黑色墨水的视觉记忆与遥远大陆的奇妙童话再难剥离。每晚入睡前,表姐都会都躺对面小床上给我念一段当天新抄的书,我至今记得,当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赛情妇时,我蒙着被子哭得泪流满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文学感动,尽管那只是小说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情节,尽管当时的我还不懂感情。
1976年文革结束,书籍在被囚禁了十几年后终于发生了一次解放,第一批重见天日的文学书多是繁体版,市民们经常天不亮就赶到新华书店前排队抢购同一本书。有一个星期天,我揣着几元零花钱,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了半天的长队后买到一本竖版的《牛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购书。那本书我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流了不知道多少次泪,李俍民是被我记住的第一个译者名。就从那时起,我对译者萌生出敬意,是他们的翻译为我打开一扇扇眺望世界并审视自己的窗。
我很赞成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不存在世界文学,只有翻译文学。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流浪的机会和挫折的财富,让我走进匈牙利文学,走上了文学翻译的路。
1991年深秋,正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我登上了横穿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经过10天的颠簸和历险,从北京到了匈牙利,将自己投进一个全然陌生的实验场,行囊里揣的唯一一本书,是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渴望生活》,再有就是自己年轻的本钱。在塞格德的一家私人诊所我只工作了4个月,突然的变故,使我一夜之间失业、失恋、失掉工作身份,接下来,是8年名副其实的流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靠当地朋友的接济,凭自己的情感能力,在我的口袋里有一大串钥匙,都是朋友们给我的,我可以随时打开他们的家门。
这么多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就三件事:交朋友,写日记,再有就是翻着字典读匈文书。
十分幸运,我刚到匈牙利不久,就结识了一位最重要的朋友——海尔奈·亚诺什,当时他在塞格德大学历史系教书,现在是匈牙利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他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收留了我,通过他,我结实了许多匈牙利作家,包括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伊姆莱、2016年获国际布克奖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能成为他们的中国声音。今天给我的这项翻译奖,也是对我生命形式的鼓励和肯定。
当然,这个翻译奖既是给我这个译者的,也是给作者马洛伊·山多尔的,客观地讲,至少在中文版的《烛烬》里,我与马洛伊是合著者。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用不着谦虚——合著者,是译者与作者在译本中的真正关系,也是最理想的关系。
我翻译《烛烬》和马洛伊的另一部代表作《一个市民的自白》,既不是遵循“信达雅”的教条,也不觉得是“带着镣铐跳舞”,翻译内容远不是目标,而是尽力让自己成为“会中文的马洛伊”,调动相应的汉语词库,在中文里复建马洛伊风格,包括他讲述的语气、声调、节奏、修辞的繁复考究和结构的沉稳细密,与其说翻译,不如说让马洛伊用中文将《烛烬》再写一遍。一边翻译,一边朗读,读完译句,再读原句,相互对照,反复润色,经常为加一个“的”或去一个“地”而琢磨多遍,感觉节奏和松紧度。实话实说,我是把《烛烬》当成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努力在从匈牙利语到中文的转换中保持原作语言诗性的纯度。中文版《烛烬》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业内同行的好评,我甚感欣慰。
一位好的文学翻译,可以给原著第二条生命;一个不好的翻译,则是原著的杀手。文学翻译在文学与文学对话中扮演的角色,确实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因如此,我在此代表我的翻译同行对吴承恩文学奖致敬,因为你们设立了翻译奖。
感谢你们,感谢编辑,感谢读者,更感谢文学。在今天,或许文学已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可以改变一个人,我自己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例子。我会一本一本地翻译下去,让更多的好书影响更多的读者,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个个体的人。
编辑: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