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古名‘菣’,一年生草本,茎直立,上多枝,具纵棱线。热解暑,除蒸,截疟。”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让中华大地上一种稀松的绿植瞬时成为世界植物的明星。人们惊讶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医学的惊人智慧,赞叹获奖者屠呦呦非同凡响的创造力欣幸中国在诺贝尔科学类奖上从零到一的突破。
然而,从发现青蒿素的1971年到如今,整整40年过去了,屠呦呦已从青颜变成白发,这个诺奖诚可谓姗姗来迟。事实上,中国的青蒿制药为世界抗疟作出重大贡献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许多人探索着,坚持着,努力着,始终不离不弃,终于迎来了对中医智慧的世界性认可。
青蒿素问世
发现青蒿素,源于上世纪的一次军事方面的援助行动。1967年美越交战,热带丛林的低湿环境让疟疾横行,双方死于疟疾者超过交火伤亡的人数,越方向中国发出求助。是年正值中国文革初潮,研究治疗疟疾新药的项目成为一次秘密的军事科研任务,代号“523”,屠呦呦便是成员之一。1971年,屠呦呦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以青蒿“绞取汁,尽服之”的方法启示,转变了一贯的高温提取方式,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成分,同年10月,100%疟原虫抑制率的物质从青蒿中成功提取,一年后,屠呦呦去粗取精,萃取出抗疟单体——青蒿素,青蒿素遂问世。

青蒿素
世界上疗效最好的抗疟药物
医学并非一门“实验室”学科,一项完整有效的医学研究,药理研究固然重要,临床验证和合成制药亦是医学发展的掣肘之处,甚至因为临床验证需直面恶疾,其艰辛繁难更甚于实验室的分离萃取。
青蒿素被成功提取时,同为“523”成员,身为广州中医学院教师的李国桥正在云南的小山寨里开展疟疾调研,获悉青蒿素显著的抑疟效果后当即展开临床试验,李国桥共做了18例青蒿素用于恶性疟疾诊治的测试,首次系统证实青蒿素对疟疾的临床效用。1975年1月底,李国桥综合四年以来的试验疗效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青蒿素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同年4月的“五二三”全国中草药协作会议上,李国桥向项目组报告了青蒿素临床疗效,也在同一年,新药初制成功,四年后,青蒿素药剂最终通过全国鉴定,成为临床抗疟的可用药物。

青蒿素
当时国际上,治疗疟疾的担纲者一直是氯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研制成功,其初始疗效颇为显著,但在与疟原虫的长期“较量”中,氯喹不堪疟原虫逐渐增强抗药性而最终败下阵来,氯喹抑疟作用直线下降,恶性疟疾于上世纪60年代卷土重来,越南求助于中国正是苦于没有合适的疗效药。因此青蒿素的研发恰逢其时,其抑疟性能近乎100%,成为氯喹唯一的可替代药剂。1982年,李国桥等人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这是中国首次将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向世界公布。而中国的青蒿素制剂则在事实上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疗效最好的抗疟药物。
青蒿素的国际“飘零”
药理研究、临床验证、制药技术一气呵成,加上国际医学杂志的认可,看起来,青蒿素“成名”并掀起世界抗疟药物的革新只是旦夕之事。但正如人类文明史所一贯上演的,重大的发现总要伴随某种专属的“延迟”,青蒿素的国际化之路同样走得艰辛、曲折,堪称一部国际飘零史。
首先是因为,传统氯喹类药物“统治”多年已成惯例。虽然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李国桥和他的团队始终致力于青蒿素类药物的研发和普及,奔走于世界各地的疟疾高发区,向人们宣传推介青蒿素,展开集中的治疗和长足的药效研究。青蒿素作为一种中医药提取物,对于只熟悉西医合成药剂的国际而言很是陌生,因而难以马上破壁。
更为重要的是,疟疾一直以来被视作公共卫生问题,在大部分对疟疾敏感—的国家中(80%在非洲),疟疾防治都是政府项目,而资金贫乏的非洲国家抗疟所用的药品很大程度上都仰赖世界卫生组织的采买和发放。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政府首选指导用药中,青蒿素不在榜上,也一直未能上榜。因为这份局限,青蒿素这一意义重大的中国发明被搁浅一载又一载,得不到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疟疾也迟迟未能得到有效克制。世卫组织于1998年就开展了“击退疟疾”计划,预计12年内将致死率降低50%,然而数据显示直到2006年,疟疾致死人数不减反增,由每年 60-80万升至100多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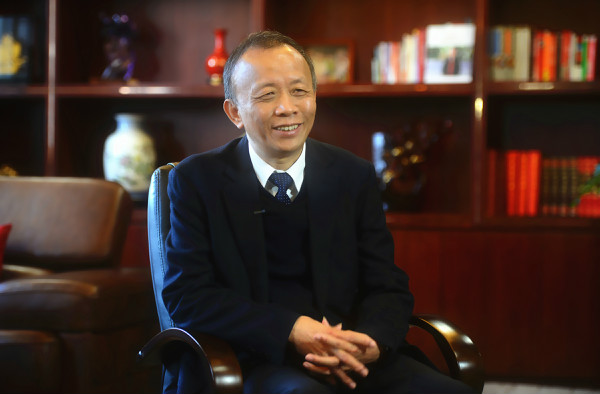
朱拉伊工作照
转机出现在2004年。一来是因为十几年的奔走为李国桥积累了许多成绩,二来,因为一个重要人物——朱拉伊的加入,中国的青蒿素药物研发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
朱拉伊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曾是李国桥的学生,李国桥在研发第三代青蒿素药物时找到他,恳请他投资青蒿产业 。面对这场不知未来本利状况的投资邀请,朱拉伊没有犹豫立即应下,在2003年投入6000万用于药物的研发,后又建成了如今中国开发青蒿素类药品的龙头企业——新南方青蒿药业。而正是新南方青蒿药业,和李国桥所在的广州中医学院,一道成为日后中国青蒿素药物研发和国际推广的核心。截止2015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与新南方集团成功研制出的第四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中文名:粤特快,英文名:Artequick),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该药具有高效、速效、低副作用、性能稳定、原料成本低、服药次数少(24小时2次服药)、保质期长、易推广、适用贫穷地区等优点,该药于2006年获得国家药监局I类新药证书。药物取得包括美国在内40个国家的国际专利保护,32个国家的商标注册,获得“第14届中国优秀专利奖、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产品称号”,取得“科技部重点新产品项目”立项,卫生部把粤特快列为我国防治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物和基本用药。2010年商务部把粤特快列为我国援助非洲的抗疟药品。现已在20个疟疾流行国家上市销售,成为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抗疟药自由市场的主要药品之一。
十几年磨出来的巨大转机确实让青蒿素有机会在国际抗疟一线发挥作用,然而,朱拉伊和李国桥很快就发现,这一转机与中国青蒿素产业发展关联甚小,更令人失望的是,青蒿素极佳的抑疟性能似乎并没有立刻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原因很简单:首先,世卫组织虽认可了青蒿素,但中国开发的青蒿素复方药却不在政府的采购单上.一直以来,只有通过世卫组织PQ(Prequalification)认证的药企才能拿到官方订单,但认证规则却堪称偏狭——只有发达国家的原创药和发展中国家的仿制药才能申请认证。这一规则将中国制药挡在门外,青蒿素“通关”最大的赢家不是中国青蒿素复方药,而是拥有预认证的两大外资药企,瑞士诺华公司和法国赛诺菲公司,他们到中国大量采购“蒿甲醚”或“青蒿琥酯”等青蒿素下游产品再制成成品药在国际出售,中国只是原材料供应方。

研发仪器
其次,青蒿素被各国用于抗疟时“方法不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防抗疟疾方法共四步:喷杀虫剂,使用杀虫剂浸过的蚊帐,疟疾阳性患者使用青蒿素复方,孕妇使用药物间歇性治疗。但事实上,这种以灭蚊为主、青蒿素治疗为辅的抗疟方案在非洲并不可行,多年和疟疾共存导致非洲人具有一定的“免疫表现”——带虫、有传染性却不发病,反复灭蚊并不能解决重复交叉传染的问题,青蒿素仅用于事后救治,而不用于事前防染,便不能实打实地发挥青蒿素的效力。
这两个原因看似简单,但却都是西方抗疟中的结构性因素和牢固的惯例传统,一时很难打破。窘境显而易见:“中国发现”的青蒿素受到认可,但“中国制造”的药物却几乎无法推广,西方市场80%的公家采购与中国无缘,而诺华公司和赛诺菲公司的挤入使私立市场也更加困难。
此外,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植物园,种植青蒿的热潮一波接一波,但因为倚赖外国公司采购,种植业发展毫无自主性——曾涨至8000元一公斤也曾跌至5元一公斤。
这一次中医战胜了西医
西方的制度偏见让李国桥和朱拉伊气愤,国内青蒿市场受制于人或许也更令他们心酸。
李国桥和朱拉伊并没有止步。2006年,两人改变了在国际青蒿素类药物私立市场“小打小闹”的策略,决心用青蒿素的疗效主攻各地政府。方法是,派技术和医疗团队到疟发国家,通过病理研究、诊疗方案设计,和特定药品匹配进行专门化的诊治,先实现灭疟,以成效为据,再图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此外,针对西方一直流行的灭疟方法的弊端——消灭蚊媒为主,李国桥团队提出“灭源灭疟法”,从消除疟原虫传播途径到清除人体中的传播祸根——疟原虫配子体,倡导全民服药,从个体治疗扩展到群体药物干预以彻底消灭疟疾。2007年,李国桥及朱拉伊团队研制出粤特快(Artequick),这个青蒿素第四代复方药具有非常鲜明的优点:疗效快、治愈率高,价格却仅为同类药物一半。因此适合穷人服用,也适合进行用于灭源灭疟的全民服用。
“用事实说话”从来都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对于医药业来说,疗效才是对药品最权威的认证。先治病再卖药的模式成功绕开了世卫组织的认证壁垒直接与疟发国家对话,李国桥和朱拉伊为这个模式起名儿:“以医带药,开辟第三方市场”。
事实证明,“以医带药”模式、“灭源灭疟法”、粤特快三者结合,成为中国青蒿素药物走进国际抗疟的前沿阵线的关键。2007年在非洲岛国科摩罗实现快速灭疟则成为验证这种新药新式新法的最瞩目“一役”。

2013年中科联合抗疟团队合影
科摩罗拥有 90万人口,但经济贫困,疟疾的横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那里出生的孩子一般要到5岁以后才会拥有自己的名字。采用西方传统的抗疟方法多年但没有效果。 2007年,李国桥带领团队到达科摩罗,先后于2007、2012和2013年在科摩罗所属的莫埃利岛、昂岛和大科岛地区展开与疟疾作战,超过220万人次参加全民服药,3万多外来流动人口参加预防服药。短短4个月时间,中国团队便将发病率降低了95%,团队还帮助该地区建立卫生点,构建防御体系,对于疗效进行长期跟踪控制和强化。经过8年努力,到2014年,这个备受疟疾折磨的岛国终于摆脱了疟疾,发病人数减少了98%,带虫率由原先的23%降到0.33%,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帮助一个国家快速控制疟疾流行。对比数据最能说明问题:赤道几内亚的传统抗疟项目中,人均花费超过50美元,三年内疟疾病例下降37.5%;而科摩罗快速灭疟项目中,人均花费低于20美元,实施后3个月,疟疾病例数下降95%;用传统方法灭疟,越南花费30年、柬埔寨14年,时间几乎是科摩罗的4倍或者2倍,但最终效果却远落科摩罗之后。此外,因科摩罗项目是中国官方援助项目,所用药物基本免费,中国青蒿素复方药物被当地人誉为天赐的“神药”。
从科摩罗项目开始,中国的青蒿素复方药、灭源灭疟的抗疟方法、与政府的合作逐渐呈现越烧越旺的局势,不仅中国的复方药被广为人知,还带动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青蒿素药物推广的执行模式:通过与疟疾高发区的政府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由当地商务部采购药品、派出工作人员。药企则提供技术培训以及疟疾防治、项目用药原则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双方合作在该地区建立卫生点,实施快速灭疟,进而构筑防御体系,彻底杜绝疟疾。
国际形势好转也促进了国内青蒿产业链日趋系统和完整,朱拉伊前后共投资15亿人民币,建成包括青蒿资源研究、草药种植、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为主导的完整的青蒿产业链条。其采用的多功能提取设备、CO2超临界萃取设备、分子蒸馏设备全自动血凝分析仪等都处于一流的设备水准;而与李国桥所在的广东中医学院这一科研基地建立的长期合作则使其青蒿素科研水平一直领先世界。目前,该公司有员工两百多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28片第四代青蒿素复方哌喹片(粤特快)。并且,截止目前,粤特快已取得40个国家的专利保护,在18个疟疾流行国家上市销售。
1974年,高中毕业的朱拉伊在家乡梅州丰顺县曾任“赤脚医生”,背着药箱,活跃于田间地头。那时,他最大的志向就是做一名出色的中医。30年后,身为企业家的他再续前缘,将中医的智慧推向世界,泽被万民。

朱拉伊回母校
靠着灭疟的决心和有效的方法,这一支从中国南部走出奔忙在世界各地的团队逐渐引来世界的瞩目。科摩罗副总统穆哈吉多次在国际会话场合向非洲各国元首介绍灭源灭疟项目的显著成果。2015年5月8日,他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呼吁:“用最科学和最富建设性的方法,不存偏见,抛开利益冲突,大家坐下来一起评审和评估我们(西方)所使用的方法。”非洲国家马拉维决定接受中国的抗疟援助,其总统穆塔里卡表明“过去50年,我们是朝西方看,但是效果并不好,疟疾疫情依旧严峻,今后马拉维要朝东方看。”,此外,索马里、南非、海地等十余国的卫生部长到广东参观考察,多个国家均表示,希望采用广东清除疟疾的技术和药物来帮助解决疟疾的威胁。
或许最令人鼓舞的胜利还是来自世卫组织的权威结论。世卫组织在2014年疟疾报告中给予青蒿素极高评价,承认在青蒿素复方药物的帮助下,截止2014年,全球疟疾发病率降低了47%。世卫组织声称“这是世界疟疾防治史上最好的一段”。对于中国团队倡导全民服药的防抗方法,世卫组织最初认为会导致抗药性因而不很支持。事实上,不同于以往的抗疟药物——抗药性指数都达100以上,青蒿素属于短伴随期,服药后3小时内即可排光,几乎不产生抗药性。大量临床试点验证后,世卫组织打消顾虑,于2015年5月采用了中国团队灭疟的方法,并号召在全球各岛国进行推广。从1975年制药成功,到如今青蒿素复方药得到世界接纳并用于全球抗疟,中国整整走了40年。
诺贝尔奖久盼终至
正如从1971年始,青蒿素从书里、论文中、实验室走向疟发区、疟疾病人和疟原虫,时隔40年,中国青蒿素复方药的成果将青蒿素的发明这一具有时代性的医学突破再次带回了医学理论界,带入国际奖评界。

屠呦呦获奖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米勒,是第一个将青蒿素推向各类有影响力的国际奖项的人。作为每年都会从诺贝尔奖评委会收到推荐表格的“固定推荐人”,米勒也被青蒿素震惊世界的灭疟效果所吸引。他,连同华人科学家苏新专,一道对于青蒿素的发明过程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最终认定,屠呦呦是青蒿素发明的最关键的人。2010年,米勒将屠呦呦推荐向诺贝尔奖和被称为诺贝尔风向标的拉斯克奖两项大奖,但只有后者作出了回应,拉斯克评审委员会得到消息后迅速着人来了解了具体情况,经过审查认定,一年后的拉斯克颁奖典礼上,屠呦呦出现在领奖台上。米勒和苏新专为了扩大青蒿素这一发明在国际上的认同,配合拉斯克奖写了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并发表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拉斯克奖和米勒、苏新专的文章相互映照,广泛地宣传了青蒿素的发明对于医学研究的突破性贡献。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几乎每一年,米勒都在诺贝尔评委会寄来的推荐表格填上屠呦呦的名字。
2015年10月5日,在瑞典皇家卡罗琳医学院举行的诺贝尔大会上,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和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共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一半共同授予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另一半则授予屠呦呦一人。给屠呦呦的颁奖词平素质朴但是撼动人心“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三人的研究的全球影响及其对人类福祉的改善是无可估量的。”
至此,青蒿素经过半个世纪的漂流,终于迎接了一场气象盛大的晚宴,可以踏实地画上一枚小小的休止符。
荣耀的背后往往藏着一个庞大的故事,历史极尽复杂,从不主动诉说自身的曲折和分量,并不是每一个故事中人都能获得一束历史投射的光芒。我们看到的历史,似乎总是把一些人拉在台前,获得倾慕与赞赏,而把另一些同样重要的人落在幕后,落在无声的岁月里和时间的静默中。对千千万万致力于让中国青蒿走向世界的无名前行者来说,青蒿素药物攻克疟疾难题,便是自己收获的最大回报。这份沉潜,正如朱拉伊在故事的背后静默不语,如李国桥在1981年注射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时写下的那句遗嘱——“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足矣”。2015年的诺奖,不仅是对1971年那场石破天惊的提取实验的赞美,也是对这个长达40年的青蒿素故事的感谢,更是对中国中医药界——这个一直被忽视的集体——荣耀的归送。
作者:陆宁波、马倩、刘玲斐
摄影:张莹
















